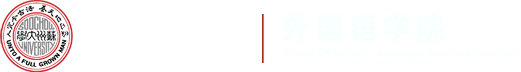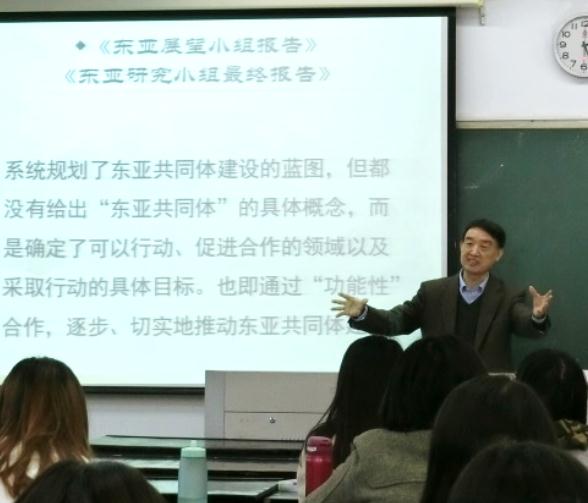亚洲共同体4月份上旬讲座简报
讲座题目: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座人:胡令远
时间:2018年4月4日,星期三13:30~15:30
地点:逸夫楼231
讲座人简历: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两岸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研究学会(香港)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等。出版专著《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等3部,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
讲座伊始,胡令远教授由“朝贡体系”的“贸易”体质、“西力东渐”的背后推手到日本的崛起、冷战时代的东亚经济合作,简述了“东亚共同体”的“前世今生”,概括其基本概念及特征,并指出在“东亚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进程中,东亚金融危机是催化与起爆剂。
接着,胡令远教授带领大家分析了《东亚展望小组报告》与《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他总结到,两份报告系统规划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蓝图,但没有界定“东亚共同体”的具体概念,而是确定可以行动、促进合作的领域以及采取行动的具体目标,即通过“功能性”合作,逐步、切实地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而后又引用温家宝的话阐述东亚合作的框架应该以“10+1”为基础,“10+3”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主要补充,充分发挥东盟的主导作用,努力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谈及东亚共同体建构的问题点,胡令远教授列举出美国的世界战略调整,中、日、东盟之间的主导权之争,文化差异等要素。
最后,胡令远教授展望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前景,认为东亚共同体与东亚海洋权益之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并相信,作为肩负重大责任的大国,中国将在其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讲座题目:观经济之形,察发展之势――从十九大看中国经济新走向
讲座人:沈健
时间: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14:00~16:00
地点:逸夫楼231
讲座人简历:沈健,江苏省委组织部苏州干部培训基地特聘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和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苏州、盐城、镇江等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苏州电视台财经顾问兼特约评论员。一直在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有24年的教学经验。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为外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曾先后赴西藏、新疆、四川、河南、内蒙、吉林、浙江、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作演讲和咨询。出版专著《中国房改的理论与实践》。
讲座开篇,沈健教授判断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提出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为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沈健教授列举许多实例,详细说明当今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与昔日相比已大为不同,因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那般,中国必须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沈健教授还强调,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两个原则,始终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全球正处于以通讯技术和能源革命相结合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之中,中国要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就需要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治理层面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坚持的战略性选择。
讲座题目:“世界名著”的创出――《吾�は猫である》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讲座人:王志松
时间: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13:30~15:30
地点:逸夫楼231
讲座人简历:王志松,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主要研究成果有:《“直译文体”的汉语要素与书写的自觉――论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体》(《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3期)、《跨越式批判――柄谷行人的文艺理论及其批评活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2期)等50余篇论文。
讲座开篇,王志松教授介绍了中国近代文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并提出翻译文学介于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具备流动性与创造性。王志松教授表示,如何看待以外语形式存在的“日本文学”,是追问日本文学研究理想状态的重要问题。综合研究日文原版和外文版,有助于探究更广泛意义上的“日本文学”的多样性与生产性。
围绕此问题,王志松教授以夏目漱石的《吾�は猫である》为例,进一步展开解说。《吾�は猫である》不仅是漱石文学的代表作,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更是同欧美名作齐肩的“世界名著”。受教育改革和商业主义的影响,21世纪以来,《吾�は猫である》的汉译本层出不穷,形态多样,包括全译本、摘译本、插图本等。一般认为原作中富有机智的前半部分内容比沉郁的后半部分内容更具备“余裕”特征,故而出现了只翻译前半部分的摘译本。
谈及书名“吾�は猫である”的翻译,王志松教授分析了几位大家的观点。其中,翻译家于雷曾坦言自己不赞成“我是猫”这一译法,理由有二,第一,原著书名并非单纯的判断文,更暗含着猫面向人类夸耀自我的语感;第二,尽管这只猫自诩为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圣猫、灵猫、神猫,却还没有名字,“我是猫”三个字难以体现这种矛盾的讽嘲、幽默的声色。翻译家刘振瀛则表示,明治38年前后,“吾�”含有“庄重傲慢”之意,是日本大臣、将军常用来自称的词,让作品中的无名之猫自称“吾�”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因此,他提议译作“咱(za)家”。事实上,关于翻译书名“吾�は猫である”的争论从未停止,学界一直在探讨如何更好地传达字面背后暗含的日本文化、时代风俗。王志松教授认为,虽然《吾�は猫である》已有许多汉译本,但都未能充分传达原作内容的多层性。